週年福音講道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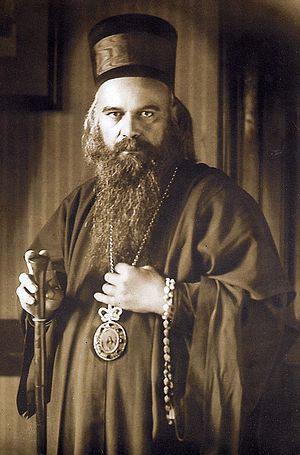
五旬節後第九主日
比自然更強者
瑪14:22-34
我們的天主是得勝者,自古至今,一切美善而持久的勝利都屬於祂。祂戰勝了罪人造成的人間混亂,重建秩序。當最卑劣者登上首位,最優秀者淪落末位時,祂便顛覆這混亂,使首先的成為末後的,末後的成為首先的。祂戰勝了惡神對人類的毒計與謀害,如強風驅散惡臭般將他們擊潰。祂戰勝一切匱乏:在稀少之處賜予增長,在空無之處賜予豐盈。祂戰勝疾病與苦痛;祂只須一言,病痛便消逝無蹤:盲者得見,聾者得聞,啞者能言,癱瘓者起立行走,癩病人得潔淨。祂戰勝死亡:祂一聲令下,死亡便鬆開緊咬獵物的利齒。祂統治著由天使與聖人組成的天上的大能者──天國永無窮盡,與之相比,世間諸國猶如母腹般黑暗狹隘。祂號令世間的元素與受造之物,凡違抗祂命令的,無不在永恆的毀滅中分崩離析。
日復一日,勝利接著勝利。這世界的歷史,就是天主一連串的勝利,彰顯祂的大能與不可抗拒。祂溫順如羔羊,但天地卻在祂面前戰慄。當祂容許自己受辱時,祂的偉大反而最為顯著地彰顯出來。當祂容許自己的面容被唾污時,祂由此揭露了凡不屬祂者的污穢。當祂將自己交付宰殺時,祂的生命反而大放光明。
天主藉著太陽揭示祂的光明,如同祂自身的黯淡投影。祂藉宇宙中無數熾燃天體彰顯大能,藉創世秩序與寰宇眾生展現智慧,藉受造之物的美顯露祂的美,藉對萬物的精心養育昭示祂的慈悲,藉一切生命彰顯祂的生命。但這一切不過是祂的黯淡短暫的影像;不過是濃煙中書寫的火字。永生天主的種種特質,已在人世以最耀目的方式顯現──並非顯現在每個人身上;不在平凡受造的人身上,而在非受造的「人」、主耶穌基督身上。一切都匯聚在祂身上;在祂血肉之軀中,光明與大能、智慧與美、慈悲與生命,一同煥發光輝。
光明若非戰勝黑暗,還有何意義?大能若非戰勝軟弱,還有何意義?智慧若非戰勝瘋狂與錯亂,又是什麼?美若非戰勝醜陋與畸形,又是什麼?難道仁慈不是戰勝邪惡、惡毒與嫉妒的勝利?而生命──豈非天主戰勝死亡的勝利?
因基督之名受洗的追隨基督者,你們作何感想?難道自世界肇基以來,基督不曾啟示所有這些勝利嗎?你們豈非日日感受到自己正追隨著世界與時間伊始以來最偉大的勝利者;豈非因那全知全能者之名受洗──祂以自身之美裝點萬物,以祂的慈悲撫慰眾生,以祂的生命賦予他們活力?若對此渾然不覺,縱然追隨祂、以祂的名稱呼自己,於你們也無甚裨益。唯有藉著主耶穌,你們方能毫不猶疑地確信:永生天主對萬物、眾元素及世間一切邪惡的勝利權能,絕對無可匹敵。唯有主耶穌能賜你們生之勇氣與穿越死亡之膽量。唯有祂能證實那受制於腐朽的易逝生命的盼望。唯有祂能在你們心中激起對一切美善的愛,因祂是天主對世界活生生的勝利。「你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若16:33),基督對門徒如此說,並透過他們向我們眾人宣告。毋須懼怕: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已戰勝世界。福音書是祂的勝利之書,是祂全能的見證。教會歷史直至今日──乃至世界終結──更是祂勝利的詳盡記錄。凡懷疑者,必不得嘗其果。因此,讓我們解釋今日福音時不存絲毫疑慮,因它記載著基督對自然的巨大勝大。
「耶穌即刻催迫門徒上船,在他以先到對岸去;這其間,他遣散了群眾。」這是在增餅的榮耀奇蹟之後──當時主以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婦女孩童尚不在內),民眾吃飽後還剩下十二筐碎餅。主此時已預見並準備了另一項門徒始料未及的至榮耀奇蹟。祂的第一項準備是讓門徒乘船渡往對岸,第二項是遣散群眾,第三項則是獨自上山祈禱。
「耶穌遣散了群眾以後,便私自上山祈禱去了。到了夜晚,他獨自一人在那裡。」經文反覆強調祂的獨處:「私自」、「獨自一人」,為要突顯主刻意尋求、且在遣散眾人後仍持續的獨處狀態。高山、獨處、黑暗──人在此境最易感知天主氣息的臨近,此時的祈禱亦最為甘飴。主耶穌一切所行,皆為教誨我們、拯救我們。祂降世不僅以言教導,更以行為、事件、乃至每個舉止動作為訓。祂登山因為那裡最為寧靜;祂獨處因為獨處意味與世隔絕;祂於夜暗中祈禱,因為這黑暗猶如眼前垂簾,能阻斷目光流連於諸般外物──這正是最妨礙心靈沉思的障礙。
基督在山上祈禱之事,也蘊涵著深奧的內在意義。遣散群眾、上山、獨處與黑暗──這一切究竟意味著什麼?遣散群眾象徵摒棄世俗所呈現的一切,以及那些將我們綑綁於世、擾亂心神的記憶,唯有掏空世俗,方能於祈禱中向天主攀升。上山是什麼意思?意即將心靈提升至天主之巔,達於祂的臨在與同在。凡汲汲於塵世者,縱使攬盡人間萬般利益與芸芸眾生,亦無法同時登臨高處──那使人獨對造物主之境。獨處又是什麼意思?意即靈魂的赤露狀態。與世隔絕之人,必會感覺到可怖的孤寂。那些因幻滅而墮入這種可怖的孤寂的人,若未能攀升至與天主相遇之高處,往往會自殺。黑暗是什麼意思?意即此世之光全然隱沒。對獨自祈禱者而言,這世界被深沉的黑暗籠罩,而來自天主的天國之光,將漸次為他破曉,照亮一個全新、不斷照耀、遠勝此世的國度。此即祈禱的四重境界及其內在意義。基督在這一境況中所行的,具體呈現為:遣散群眾、上山、獨處與黑暗。
主耶穌獨自祈禱,其前因後果──此前發生之事與此後將發生之事──對我們亦具教誨意義。在前往祈禱之前,主剛行了前所未聞的增餅奇蹟,而隨後祂將如履平地般行至湖中心。縱使這兩項奇蹟皆憑藉祂自亙古以來便擁有的神能所行──這能力在祂於肉身內旅居塵世期間從未離棄──祂仍在會堂中與眾人一起祈禱,亦在曠野獨自祈禱。我們很難參透主耶穌這些祈禱背後奧秘的個人動機。顯而易見,藉著這些祈禱,這位永恆之父的獨生子持續見證著祂在地上與父及聖神不可分的合一。
除此之外,主祈禱的這一典範中更蘊含著明確教導:善工必先於祈禱,如此祈禱方能助益善工。我們必須先以善行見證我們的信德,再以言詞宣認信仰。然而,唯有當我們預備行善時祈求天主助佑,只有這樣,祈禱才具有價值。為惡事而祈求天主相助,不但徒然無益,實際上還是褻瀆之舉。為行惡而祈禱,猶如播種毒麥卻妄求天主使之長成良麥。每行一善後,我們當即祈禱,感謝天主使我們堪當並有能力完成此善工;每行一善前,亦當祈禱,懇求天主恩寵、助佑與合作,使我們眼面的善工臻於至善至美。簡言之,我們所擁有、所施行、所經歷、所見聞、所閱讀的一切美善──無一例外──皆當全然歸功於天主,而非我們自己:我們的能力、才智或義德,因我們在主面前實為虛無。當主耶穌行了如此之大的奇蹟後,仍向與祂同為永恆、同一性體的父及聖神展現溫良、謙卑與順服,我們這些由虛無中受造、離開天主的助佑片刻不能存活、更遑論行善的受造物,豈能不向造物主展現溫良、謙卑與順服?
「船已離岸幾里了,受著波浪的顛簸,因為吹的是逆風。夜間四更時分,耶穌步行海上,朝著他們走來。」當門徒傍晚啟航時,湖面原本平靜,不料風向驟變,波濤驟起(此湖常會發生這樣的事),船身劇烈顛簸,眾門徒驚懼不已。主耶穌早已預見這一切,卻刻意讓門徒身陷險境,為要使他們體悟離了祂便全然無助,更為堅固他們對祂的信心;為要喚醒他們記憶──昔日海上風暴時,祂同在船中,他們驚惶喚醒祂,呼喊著:「主!救命啊!我們要喪亡了。」(瑪8:24-25)此刻必切望有祂同在。更為使他們預先認識到祂離開他們前所說神聖話語的真理:「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15:5)
在先前那次海上風暴中,門徒們經歷的試煉較小,他們信德所受的考驗也較輕,因為祂雖在船中睡著,卻仍與他們同在。如今在這第二次風暴中,他們面臨的試煉更為嚴峻,信德所受的考驗也更為艱難。祂不在場,遠離他們,在山上,在荒野裡。他們如何向祂呼求?如何讓祂知曉他們的困境?能派誰去傳話說:「主!救命啊!我們要喪亡了。」沒有人可派。門徒們看到自己面臨喪亡的威脅。彷彿一個遵行天主旨意的人竟會喪亡!這對義人是何等奇妙的教導:他們不該在天主安排的道路上絕望;他們該相信那位打發他們上路的主必看顧他們,也知曉他們遭遇的危險。然而天主並不急於施援;祂要試煉義人的信德,如同金子在火中精煉一樣。
當門徒們陷於極端絕望的境地時,基督突然向他們顯現,行走在水面上。這事發生在「夜間四更時分」。猶太人如同統治他們的羅馬人一樣,將夜間分為四更,每更三小時。主在夜間第四更,即黎明前的末更,向門徒們顯現。
「門徒看見他在海上行走,就驚駭說:『是個妖怪。』並且嚇得大叫起來。」當時或許天已破曉,或是月明之夜,又或是主在黑暗中帶著大博爾山的光輝顯現;我們不得而知。重要的是,祂讓門徒們看見了祂。門徒們看見祂在水面上,心中充滿難以言喻的恐懼。這種新的恐懼比他們對風暴及其所帶來毀滅的恐懼更甚。他們不知道他們的主竟有如此能力,對自然界有這般權柄;祂此前從未向他們顯露過。他們只見過祂命令海洋與風浪,卻不知祂竟能如履平地般行走在水面上。當然,他們本應、也能從先前的奇蹟中推論出這一點,因為那能命令風平浪靜的主,無疑也能如履平地般行走在水面上。但門徒們在靈性上尚未成熟;他們的信德仍然薄弱。基督施行這個新的奇蹟,正是為了堅固他們的信德。
「門徒就驚駭說:『是個妖怪。』並且嚇得大叫起來。」那是個妖怪,或許是撒殫自己偽裝成他們的師傅。他們知道且曾見過他們的師傅在這世上與撒殫及其大軍爭戰。而此刻──他們可能會這麼想──撒殫趁此極度危險之際,要來折磨並殺害祂的朋友們。他們什麼念頭沒想過?當然,在我們這個時代,那些行走在天主的道路上卻膽怯的人,在危險中會想到的一切,他們也都想到了。
這就是天主對待祂所愛之人的方式。「因為上主懲戒祂所愛的,鞭打祂所接管的每個兒子。」(希12:6)按金口聖若望的理解,祂以最大的苦難作為其所受苦難的終結。祂在塵世的一生中飽受磨難,當祂來到終點,獲得勝利時,祂承受了最大的苦難──被釘十字架並埋葬於地中。但這最大的苦難很快就過去了,隨後黎明到來,藉著復活達至最終的勝利。
後來,許多為基督教信仰殉道者也經歷了這樣的苦難:先是小苦難,然後越來越大,直到面臨死亡本身時,他們遭受了最大的苦難與誘惑。這裡僅舉千萬例子中的一個:異教徒用越來越殘酷可怕的方式折磨聖女瑪利納。他們最終將她赤身綁在樹上,開始鞭打她,直至皮開肉綻。她傷勢極重:鮮血流淌,剝落的皮肉間露出森森白骨。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苦難嗎?不;這位天主的聖女還要面臨更大的考驗。到了晚上,他們將傷痕累累的她投入監獄。在漆黑的牢房裡,夜間有個恐怖的幻影來訪:邪靈以巨大醜惡、斑紋可憎的蛇的形象,先是纏繞著這位聖潔少女蠕動,繼而將她全身纏住,並用骯髒的顎咬住她的頭。但這並未持續太久,因為天主從不讓祂忠信的僕人承受超過其所能忍受的誘惑。緊接著,當瑪利納全心向天主呼求,並在心裡劃了十字聖號時,那蛇便消失了,諸天在她上方敞開。她看見十字架在不可言喻的光輝中,頂端停著一隻白鴿,並聽見這話:「歡欣吧,瑪利納,基督的理性之鴿,因你已戰勝那邪惡的仇敵!」
基督的門徒們也經歷了類似的事。在經歷海上風暴的極度恐懼後,更大的恐懼臨到他們:那看似妖怪的存在。然而這並非妖怪,而是奇妙且拯救的現實;不是夢境,而是異象;不是假扮基督者,而是主基督自己。
「耶穌立即向他們說道:『放心!是我。不必害怕!』」你可看見主如何不讓祂自己的子民在最大的試煉中長久受苦?祂知曉他們的恐懼,知道他們因那看似妖怪的存在而驚惶,於是立即拯救他們脫離這恐懼。「耶穌立即向他們說道:『放心!』」立即!你可看見祂如何賜予他們勇氣,可說是將他們因恐懼而幾乎喪失的生命氣息重新賦予他們:「放心,是我;不要害怕。」何等奇妙的聲音!何等賜予生命的話語!魔鬼聞聲逃遁,疾病退散,死者復生。這聲音創造了天地、日月星辰、天使與人類。這聲音是一切美善、生命、健康、智慧與喜樂的源頭。「放心,是我!」這些話並非人人得聞,唯有為主受苦的義人方能聽見。並非所有受苦者都能聽見基督的聲音。那些因罪惡與不義而受苦的人,豈能聽見祂?唯獨為信仰祂而受苦之人方能聽見(參閱伯前4:13-16)。此處門徒們正是為信仰基督而受苦;更確切地說,是為使他們對基督的信德越發堅固。
「伯多祿回答說:『主,如果是祢,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裡罷!』」伯多祿這話既表達出他的喜樂,也顯出他的疑惑。「主,」是喜樂之心的呼喊;「如果是祢」則透露出懷疑。後來,當伯多祿在信德上已得到堅固時,他就不會這樣說了。當復活的主在這同一革乃撒勒湖邊顯現,伯多祿聽見若望說:「是主!」……「就束上外衣,縱身跳入海裡」(若21:7)。那時他既不懷疑是主,也不懼怕跳入海中。但此時他仍是靈性上的初學者,仍心存畏怯,因此他說:「如果是祢,就叫我步行到你那裡罷!」
「耶穌說:『來罷!』伯多祿遂從船上下來,走在水面上,往耶穌那裡去。」伯多祿能走多遠,全憑他的信德有多深;但當懷疑一侵入,他立刻就開始下沉,因為懷疑招致恐懼。離開船隻、在水面上走向主耶穌的內在含義,就是要使靈魂超脫肉身的牽掛與俗世之愛,踏上通往屬靈世界、通往救主的險途。這種時刻也會發生在普通信徒身上,發生在那些對基督既懷喜樂又存疑慮的怯懦者身上。他們常渴望擺脫肉身的束縛跟隨基督──屬靈世界的君王,卻很快感到自己正在下墜,於是又回到肉身的牽絆中,如同回到風浪中的船裡。唯有那些具有巨大屬靈身量的人──人類中最偉大的英雄──才能憑藉長期堅固的信德操練,從肉身的船隻出發,在波濤洶湧的屬靈海洋中迎向基督君王。唯獨他們深刻地經驗到離船時的恐懼、風暴中的驚惶,以及面見基督時無可言喻的喜樂。保祿宗徒在世時就經歷過這種靈魂脫離肉身之船的過程,此後許多聖人經歷過。這險途終點的喜樂與甘飴何等巨大,從他歡欣的呼喊即可見一斑:「對這樣的人,我要誇耀」(格後12:5)。
現在讓我們看看當時仍怯懦的伯多祿遭遇了什麼:「但他一見風勢很強,就害怕起來,並開始下沉,遂大叫說:『主,救我罷!』」為何風能使他驚懼,而海卻不能?就像一個初學步的幼童:他走了幾步,但只要有人一笑,這孩子就會跌倒在地。我們的屬靈熱忱也是如此:最微小的阻礙就能使我們跌倒退卻。
「耶穌立刻伸手拉住他,對他說:『小信德的人哪!你為什麼懷疑?』」我們豈不是千百次在這生命危險的海洋中沉溺,直到某隻看不見的手抓住我們,突然將我們拉出險境?我們當中誰不能舉出幾個這樣的例子?我們都知道這事,也一再談論,甚至承認那拯救我們的看不見的手確實存在。但不幸的是,我們當中極少人曾藉著良心,聽見那看不見的嘴唇所發出的責備:「小信德的人哪!你為什麼懷疑?」我的朋友,你為何懷疑天主的手就在近處?為何你不在最危險的時刻光榮天主?亞巴郎獻上獨生子作為祭品時(創22:1-18),豈不是毫無懷疑?天主那時沒有拯救他嗎?約納在魚腹中不是光榮了天主,因而獲救:「當我的心靈在我內衰弱時,我懷念了上主,我的祈禱達於你前」(納2:7)。三聖童在烈火窯中(達3:19-26),還有那具有遠見卓識的達尼爾在獅子坑中(達6:16-23),以及受創傷、滿身毒瘡的約伯(約2:7-10),豈不都毫不懷疑,反而因他們的信德而得救?還有那成千上萬為基督信仰遭受極刑的人──他們是如何毫不懷疑的?那麼,我們為何還要懷疑?天主多次用祂看不見的手拯救我們,遠超我們的預期,儘管我們懷疑祂的救助。因此,我們現在必須銘記天主的恩惠,為我們的怯懦而悔改。我們必須在信德上成長,這樣在未來每次危難中,都能光榮主、呼求祂的名,我們必得救贖。讓我們在危險中光榮天主,而非僅在危險過後才光榮祂。
然而,即便我們曾表現出怯懦,也不該絕望。伯多祿也曾怯懦,但主堅固了他的信德。許多聖人中的至聖者,起初也是怯懦的,後來卻在對基督的信德中變得堅定不移。請聽聽真福達味所說:「我依靠天主,血肉之人豈奈我何!天主,我要向祢還我所許的願,我必向祢獻上讚頌的祭獻。因為祢救我脫離死亡,使我不敢跌倒。」(詠55:11-13)真正相信者這樣說,他憑經驗知道:天主連我們的頭髮都數過了,沒有一隻麻雀能在天主不知情的情況下墜落──更遑論人了。
「他們一上了船,風就停了。」基督剛登上船,風浪便止息。這風並非自行停歇,而是聽從主耶穌的命令而止。雖然此處沒有像先前那次明確記載基督斥責風浪(瑪8:26),但祂確實如此行事的跡象再明顯不過。聖瑪竇無疑認為,風浪是順從基督那未說出口的內在命令而平息。正是憑著祂的大能與意圖,風浪才得以止息。基督登船平息風浪的內在含義十分明顯:當生活的主耶穌進入我們身體這艘船──無論是通過聖體聖事、祈禱或其他蒙福的途徑──在我們內的情慾風浪便會平息,這艘船也將安然駛向彼岸。
「船上的人便朝拜祂說:『祢真是天主子。』」當主首次平息海上風浪時,門徒們如同其他軟弱的常人一般問道:「這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竟連風和海也聽從他!」(瑪8:27)。但自那時起,他們已目睹了導師行的許多奇蹟,聆聽了大量教誨,信德因而得到堅固。如今面對這個偉大奇蹟,他們不再詢問「這是誰」,而是跪伏在祂面前宣認:「祢真是天主子!」這是眾門徒首次集體承認耶穌為天主子。猶達斯當然也在其中,也宣認了祂。然而他後來因貪婪徹底否認了自己的主與導師。伯多祿確實也曾三次否認祂,但伯多祿的否認是出於恐懼的衝動之舉,且立即痛悔哭泣。「船上的人便朝拜他」,並承認祂是天主子,這段經文的內在含義,對每位基督徒都極具教益。當主一旦居於我們內,在我們內的一切──我們的理智與全部思想,我們的心靈與所有感受,我們的靈魂與一切渴慕──都應當朝拜祂、宣認祂的名。如此,我們整個身體將充滿光明,毫無黑暗。但若我們領受基督後又因罪惡驅逐祂,或如猶達斯般否認祂,我們就有禍了!這後來的景況比先前更為不堪,因為當基督離開猶達斯時,「撒殫進入了他的心」(若13:27)。我們切莫忘記:絕不可玩弄天主,如同玩火自焚般自取滅亡(希12:29)。
「他們渡到對岸,來到革乃撒勒地方。」他們抵達了所要前往的葛法翁城附近(參若6:17)。凡是去過加里肋亞的人,多少能想像這場風暴把基督的宗徒們吹離航線多遠。貝特賽達和葛法翁都位於湖的北岸。門徒們從貝特賽達下方登船時,本只需沿岸航行即可。然而經上記載,船被風暴吹到了湖心。正是在湖中央,主踏著波浪而來,顯現給他們。風暴平息後,船必須駛回葛法翁下方的岸邊。根據瑪竇和路加的記載,這次船似乎是藉著風帆和船槳自然渡過的,但若望的敘述卻讓人得出結論:主運用了祂不可抗拒的大能,使船立刻抵達港口,因為他寫道:「船就立時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若6:21)。聖史們的記述在此毫無矛盾,因為那位能在水面行走、以言語和意念平息風浪的主,若有必要,無疑也能使船瞬間抵港。若望這句話的內在含義是:當主來居住在我們內時,我們便感到自己如同置身天國的安全港灣,生命之舟不再受風浪侵擾。此後,縱使仍需行走於塵世,我們也感受不到這些,我們的心神已活在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得勝的基督統治的國度。在祂的勝利中,我們欣喜地看見自己的勝利,而祂的勝利也在我們的勝利中彰顯。
唯有祂是得勝一切邪惡者,唯有祂不允許自己被任何邪惡所勝。因此,我們在祂大能的羽翼之下庇難,那裡既無風暴也無狂風,更無幽靈妖怪,「既無痛苦,也無憂傷,更無哀嘆,唯有永生」(引自亡者集禱頌)。在那裡,我們將豐盛地尋得一切美善:這些美善不再如塵世之物會遭蟲蛀鏽蝕;在那裡,我們將與眾天使與諸聖一同讚頌基督的勝利作為──這些偉業在我們這必朽的生命中,在這有限的視野裡,實難領會。但到那時,一切都將向我們顯明,我們將歡欣雀躍,而這喜樂將永無終止。願讚頌與光榮歸於主耶穌,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